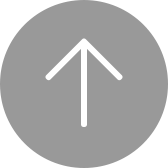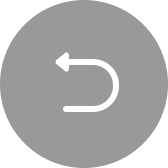那天下午坐在电脑前敲字,桌上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,响得那样突兀,心猛地抽搐了一下,一看果然是父亲的男保姆老刘打来的。接通后,老刘说父亲气喘得很,一天都没吃了,你来看看呀。撂下电话,骑车直奔父亲家。
86岁的父亲一直一个人住。哥哥定居北京,弟弟定居苏州,母亲故去后,我让他跟我住,可他说什么也不肯,我知道那是因为他十分依恋他的家。父亲患有严重的高血压、心脏病、哮喘、前列腺炎等,个个都是悬在头上的刀,我不放心但又无奈,就替他找了个男保姆照料他。
很快就到了父亲家。一座老式的旧楼,前面一个小院子,院子里长满了花草。平时父亲就坐在院子里看着花草发呆,想那早已飘零的往事。屋内的家具均已年老破旧,沉淀着岁月的斑驳。我曾经买来新的桌凳企图取而代之,但是都被父亲拒之门外。父亲摸着虽然陈旧但油光可鉴的家具犹如农人抚摸农具、外科医生抚摸手术刀一样熟稔亲切。我知道这个家是父亲缔造的,处处都有父亲自己和母亲遗留下的气息,这些气息是父亲赖以生存的力量,我连一块砖头都休想搬走。
我走到里屋,父亲面向床里,背对着我,重重的喘气声从他的喉头使劲地迸出。老刘说父亲不肯去医院,你劝劝吧。
父亲是须臾都不愿离开这个家。母亲是在医院离世的,母亲故去后,父亲一直自责说对不起母亲。他早就叮嘱我,若是他不行了,一定要留在家里,千万别送医院。
我劝父亲,你寿享还没到,只要到医院接一下氧气,你可以活过90岁的。劝了一会儿,父亲勉强同意去医院了。
许是路上的颠簸,到了医院,父亲的病越发重了,稍翻个身,他就趴伏在病床上气喘如牛,面色紫胀,口中呻吟,要求回家。吸氧根本不顶用,医生用一种特制的药放在口腔内吸,才能暂缓,而这种药不能多吸,吸多了就不起作用了。
看着父亲浑身插满各种颜色的管子,像个大蜘蛛,我的心一阵阵往下沉。医生对我说,老爷子的生命体征极不稳定,得赶快转入重症监护室。父亲坚决不肯。医生不容置疑地说,到医院就得听医生的。父亲被强行送入了全封闭的重症监护室。医生叮嘱,家属必须24小时在外候着,随时有医嘱。
重症监护室外没有床,只有一块空地,家属们用旧报纸垫在地上,上面放着从家里拿来的两床被,一床垫,一床盖。那时正是寒冬腊月啊,人吃得消吗?可就是这样的床也铺满了。我看看已没有空地了,就让老刘回家休息,自己坐在地上守候。至天亮,老刘换我回去休息。
我们交由护工送进去的饭菜,几乎没动又送出来。护工说,这老爷子不知哪来的精神,一直闹着要回家,饭也不吃,吵得不行。我想,为了回家,重病的父亲爆发了身体的全部潜能啊。我泪流满面。
至下午3点,是家属进去探视的时间。我像颗子弹迫不及待地发射了出去。老远,就看见父亲昂着头在向我招手,我扑了过去。父亲伸出手,一把握住我的手,说,儿啊,我可看到你了,在这像坐牢,带爸回家吧。父亲像孩子一样满含希望眼泪汪汪地看着我,我忽然想到我小时候要父亲带我出去玩,我也是用这样的眼神看着他。
探视的时间快结束了,医生要我出去。父亲紧紧地抓住我的手不放,坚决而执拗地说,别走。我跟医生说,你看我爸的身体不至于住这里吧,闹得你们和其他病人也不得清静。医生想想也是,说,你如果能找到其他医生接收的话,我可以让他出重症监护室。父亲看着我说,你去替我找医生,我要出去。我使劲地点点头,父亲依依不舍地松开了手。可是我跑遍了心脏科、呼吸科、泌尿科,他们都不肯接收。我知道,父亲的病太重,他们怕出事,都不敢收。最后,只好找到院长,说父亲不适宜在重症监护室。院长了解情况后,从中斡旋让呼吸科收了下来。
从重症监护室出来后,父亲兴奋得像过年,和同舍病友们谈笑风生,痛痛快快地吃了半碗饭、喝了一碗汤,根本不像一个病人。
父亲抓住我的手说,儿啊,别离开我。过几天,我就可以回家了。但是,父亲毕竟是个病人。兴奋过后,又发病了,喘成一团,几近窒息。医生跟我说,你父亲这座老屋太朽了,四面漏风,你们准备着吧,当然我们会尽力医治的。然而父亲只要稍微好些,就跟我说,过几天我就可以回家了。
也许,老天也感动于父亲回家的执着,他的哮喘间隔时间一点点延长,一天天奇迹般地好了起来。十天后,医生宣布,老爷子可以回家了。父亲笑出了眼泪。
我用轮椅推着父亲回家,拐进家的那条巷子,他示意我停下来。他站起来不用我扶,快步扑向家门,干枯的双手颤抖地抚摸着门把手,喃喃自语,家啊,我回来了。
我打开家门,扶着父亲穿过院子。他跟院子里的花草说,花瘦了,草肥了。进屋后,他将家里桌椅橱柜等物件一一摩挲,连床头的痒痒挠也不放过,拿起来又放下,最后捧起桌上母亲的遗像贴在脸颊上说,老婆子,我出去了几天,回来了。(作者:江苏省高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朱玲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