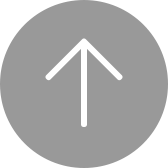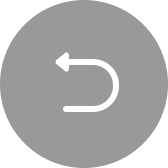自我、本我和超我
在我差不多读小学的时候,家里的书柜里有一本书,叫作《梦的解析》。后来才知道,这是大名鼎鼎的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著作,也是精神分析的奠基作品。这本书让我知道了,梦是愿望的达成,梦是潜意识的投射。也是在这本书里,弗洛伊德首次提出了本我的概念。
本我就是快乐至上的那个我。在婴儿刚刚出生的时候,只有一个人格结构,那就是本我。饿了就要吃,困了就要睡,只关心如何满足自己,不会受制于任何外界的约束。
弗洛伊德认为,本我是无意识的,是不被觉察的。在某些时候,在性本能和攻击本能出现时,也许本我会浮出意识的海面换一口气。
与本我一同构成完整人格的,还有自我和超我。
自我遵循现实原则,负责控制本我盲目的冲动,负责与外部世界的联系。在现实中,由于本我的冲动并不能被现实世界所接受,会对自我构成威胁,所以,自我往往会花费很多的能量,把本我的冲动控制在意识层面以下。
超我实现了完美的部分,代表道德评判、社会理想、兴趣爱好、个人价值。超我通过抑制本我的冲动,说服自我,按照符合道德评判的方式来做事。超我特别强大的人,往往会面对更多的羞愧感和罪恶感。
弗洛伊德认为,人格就是这三部分组成的。在我们获得完整人格的那一天起,永远都会存在放纵自我(本我)、面对现实(自我)和遵循道德(超我)之间的矛盾斗争。
这样听起来,人活着确实是挺累的。
苏醒室的两个故事
我是一名麻醉医生,在临床中发现在人刚刚麻醉苏醒的时候,问什么就会答什么,让干什么就干什么。由于麻醉药物完美的逆行性遗忘效应,一点记忆也不会留下。
在麻醉苏醒过程中,为了判断人的意识是不是恢复,需要问患者很多问题,要患者做一些不常做的动作,用来判断意识是否恢复,指令动作能不能完成。
有人说,苏醒室里每天都会上演着人生终极大戏。
你是谁?(你叫什么名字?)
你从哪里来?(手术做完了,知道吗?)要到哪里去?(自己的床号知道吗?)
对于大多数患者来说,这三个问题都可以脱口而出。只有拿到了苏醒室医生授予的“哲学学位”,才可以顺利“毕业”,返回病房。
而有些患者,就没有那么顺利“毕业”了。
人在刚刚苏醒的时候,意识会处于一段比较模糊的状态。本我、自我和超我并非同时苏醒过来,有时候,我们会看到一些有趣的现象。
一个年轻姑娘做完手术,睁眼之后,拔出气管插管。我问她,你叫什么名字,她脱口而出了自己的名字。我再问她,你的床号是多少?她停了几秒钟,说对了。我再问她,你的身份证号码是多少?她停了更长的时间,告诉我,她想不起来了。
注意了,是想不起来!并非是不想告诉我这个连脸也没看全的陌生人。
所以我认为,在正常情况下,自我会先于超我醒过来。自我掌管着现实原则和外部世界,一问一答,再也正常不过,然而,代表着自律性和警觉性的超我,似乎还在呼呼大睡。
后来,我又遇见了一个年轻男人,也是同样的苏醒拔管,醒来之后,没等到我开始问问题,他
开始自言自语起来。
“你们放开我,干什么啊,你们是不是要把我杀掉!”说着说着就要爬起来,挥舞着拳头就要抡上来。我惊呆了,第一反应是躲开,但是,出于麻醉医生的本能,我立即用上了终极“武器”——异丙酚+右旋美托咪定。效果是立竿见影的,患者马上就被“放倒”了。
他第二次醒来的时候,一睁开眼就开始说话,“你们是怎么搞的,怎么还没有弄好,让我怎么办啊!……我保证,我向你保证好不好!……宝贝儿,怎么了,宝贝儿……”
我和同事全都蒙了,人格分裂的大戏是不是已经上演了?
出于“苏醒室毕业委员会”的职责,我开始了三条终极提问。但是,他根本就不理我。
过了大概半个多小时,我重新去看他,此时此刻,他就像没事人一样,毕恭毕敬地问我,手术做好了没有?主刀医生是谁?现在几点?什么时候能吃东西?
太神奇了啊!我似乎看到了一场本我自导自演的大戏,而在这一场戏中,自我和超我都消失了。我问他,你是做什么的?他说,自己是某个公司的中层,压力山大,桃花不少。
所以,我一直很想知道,本我、自我和超我在进行切换的时候,人的脑子里究竟发生了什么?似乎人的大脑是一个高深莫测的黑箱,透过心理学量表的窗口,窥见的东西实在是太少了。
用技术“看见”大脑活动
别着急,有一门专门研究这些内容的学科,叫作神经心理学,是由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在1929年首次提出的。神经心理学,是通过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研究心理问题。这个跨学科跨得相当有水平啊,前提是,认为一切心理学现象必定伴随着大脑的生理病理活动。
神经心理学中,与临床医生息息相关的一个方面,叫作临床神经心理学。而研究的绝对热点,就是认知功能的神经影像学,简单来说,就是通过各种脑成像技术“看见”人们思考的过程。
在空间领域绝对胜出的是功能磁共振成像(fMRI),1991年美国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的医生们,利用磁共振成像反映脑血流的变化,能够对特定的大脑活动皮层区域定位,达到毫米级别的空间分辨率。比如,几秒钟的思维活动,就能够被影像所捕捉到。
但是,基于血氧水平依赖(BOLD)的fMRI技术,测量的并非是直接的神经活动,而是由神经活动引起的周围血管、血流代谢等次级生理反应的综合效应。
在时间领域绝对胜出的是脑电图(EEG),1929年,人类的脑电波被首次记录到,然后再绘制成不同幅值随时间变化的平面图,时间分辨率达到毫秒级别,记录大脑内神经元的放电活动引起头皮表面或皮层的电位变化。
越来越多的精神疾病,都通过各种脑成像技术“看见”了罪魁祸首的脑区或异常区域,为单纯的量表诊断提供了强大的后盾,在某些疾病中,功能成像技术有望取代其他方法,成为诊断疾病的“金标准”。
这些年来,EEG在麻醉领域的探索逐渐深入,基于频谱分析法的脑电双频谱指数(BIS),已经用于监测麻醉深度,告诉麻醉医生哪些患者麻“深”了,哪些患者麻“浅”了。
在谵妄领域,EEG也占领了一席之地,发病当时的脑网络连接异常,以及部分脑区波幅和频率的改变,都预示着脑成像技术能够作为辅助诊断的潜力。“看见”患者的大脑活动,而不是在黑箱之外捉迷藏。
假设说,现实世界中,本我总是存在于意识水平之下,看不见,摸不着,既是动机,也是本能,既是快乐,也是祸害,我们没有办法了解。如果本我能够“自发自愿地”在某些苏醒阶段的患者身上出现,从而通过技术手段被研究,那么,人认识自己,是不是变得更有可能了呢?